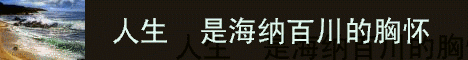
春游三道关
前几天,与朋友到市郊西北处的三道关去了一趟,忽然发现,这儿的景致奇美、奇妙,出人意料。
一般来说,要论山水景致,山青水秀,石怪洞幽,四者皆备,方为上乘。而三道关名气虽然不大,却有此四绝,令人惊诧。
山不在高,有石则名。一到三道关,只见东、西、南三座山鼎足而立,树木青葱,山石翘挺,与周围的山丘迥然不同?其中尤以东面一座为秀。远观山头,怪石林立,足使文人墨客忽发奇想,引诗制词。从山脚沿石缝草径缘石而上,身边座座巨石,如笋、如柱、如壁,小者可资攀援,大者仰视不见顶。脚下蜿蜒曲折,坎坷惊险。站在山顶巨石之上,回眸而望,周围怪石,各具姿态,或如黑熊慵懒,或如石猴矫健。山脊北侧,有一大若禅室的巨石,翘支石座之上,危如累卵,似乎一臂之力便可将其訇然推下,其奇其妙,比得上著名的“风动石”。
更绝的是左侧山脚有一石洞,幽不可测。洞中无水,走入洞中不及二十米远便觉满目漆黑。我们没带电筒,只好把随身带的纸张等可燃之物倾囊拿出点燃,借着火光,快步疾走,不知走了多远,所有的纸张烧尽,仍不见洞的尽头,不敢再走下去,只好原路退回,终不知洞深几许。
山谷中有一条小溪,从西向东潺潺而流。水极清澈,据说是山后的两眼山泉汇集而成,若真是只凭两眼山泉为源头,这泉也够旺的了。朗日之下,涉水濯洗,身上的暑气倦怠一扫而光。水极凉,令人不能久驻水中,可知泉水为源的话是不谬的。溪水跌宕疾徐,分流聚合,别有情趣。溪流中零星散布着一些巨大的石块,日蚀水消,棱角全无,平整如砥。凭石而望,野餐聚会,下有溪水消暑,上有山石悦目,足以“与君一醉一陶然”了。
在百亩方圆之内,聚此诸多景物,兼有山石耸秀,泉水清泠,岩洞幽深,林木葱笼,虽无五岳之恢宏气势,却得谐趣园之精微神韵,盛夏之时,游此佳境,实在妙不可言。
牡市已被开发为经济试验区,若将三道关稍加修整,辟为一处旅游风景区,想必大有文章可做。
《牡丹江日报》1989年5月16日
依稀小人国
好久没有真的到农村去了,记忆的深处,仍然留着第一次在乡村生活的美妙印迹。那是上中学的时候,正是文革中期,书不怎么念,却提倡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。每年春秋农忙时节,都要到农村去经风雨,见世面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那一年春天,我们去下乡劳动,地点在牡丹江畔柴河沟里的一个小山村。浴着明媚的春晖,我们班50多个学生背着行李,在柴河火车站下了车,然后沿着森林小火车的铁道线向山沟里走。拉着木材的小火车象玩具一样,冒着白烟在密林里跑,我们都觉得很新奇。我记得很清楚,第一站是佛塔密,虽然只是深山里的一个小站,但作家曲波在小说《林海雪原》中曾经提到过这个地方,来到这里便使人感到既亲切又神秘,似乎我们正走在当年侦察英雄杨子荣战斗过的地方。
筋疲力尽地走了好久,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,一个紧靠牡丹江边的小山村。小火车在这里设了一个站,叫红旗站,这个村也就叫红旗村。为了欢迎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,憨厚朴实的村民早就做好了饭菜等我们,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顿饭,金黄的玉米面大饼子,外加炖窝瓜汤。
我们都分别住在老乡家。我的房东是一对老两口,孩子都大了,分出去过。因为我爱画画。房东大爷特意把村里一个爱画画的孩子领来跟我认识,那是一个黑红脸膛的男孩子,比我小一点,也就十四、五岁的样子,名叫许凤和,眉清目秀的,脸上的皮肤有着金属般的光泽。农村的孩子特别好客,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。许凤和带我到他家去玩,拿出他的画让我看。都是一些文革时时兴的宣传画,其中还有用青白的桦树皮做的毛主席画像。
我们干的农活是拔谷子,就是给半尺多高的谷子间苗,这在农村是最简单最轻松的活。但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,只干一会儿就弯得腰疼,总得经常直起腰来东张西望。碧绿的谷苗盖满了山脚坡地,地头的山上是茂密的柞树林。我猛然看见,柞树林里有些人在忙着什么,许凤和也在那儿。干活休息的时候,我跑过去看,原来他们是在养柞蚕,他指给我看,只见宽大嫩绿的柞树叶上,爬着许多粗大的绿虫子,他们养蚕人干的活就是把吃光了树叶的蚕虫连树枝一起折下来,送到别的树上去。
午饭后休息的时候,许凤和来找我,他神秘兮兮地从衣袋里掏出东西让我看,我看时,却见是几只蚕蛾。“你敢吃吗?”他向我问道,并真的拿起一只蚕蛾,扯掉翅膀,把蚕蛾活生生地放进嘴里。我吓了一跳,愣愣地望着他,他一边吃一边说:“蚕蛾好吃,每年这时候,队里都把产完籽的蚕蛾卖给社员。”他又扯掉一只蚕蛾的翅膀送到我的眼前,让我吃。蚕蛾的爪子还在蠕动,我心里发怵,但还是接了过来,果断地放进嘴里。许凤和显得十分高兴,他搂着我的肩膀,“走,我领你去看王八晒盖儿。”我们一阵风地跑到江边,他指着江中沙滩上的大石头让我看,“一到天热的时候,王八就爬到大石头上晒盖儿。”顺着他的手指望去,果然看见几只黑灰色的鳖趴在石头上,鳖盖在阳光下闪着暗淡的光泽。“能逮着它们吗?”我雀跃地问,恨不得马上捉一只来玩。“逮不着,那王八可精了,没等你到跟前,一有声响,它们早就跑了。”说着,他捡起一块石头,嗖地撇了过去,“嗵”的一声水响,只见那些鳖们一翻身,咕碌碌地滚到水里,眨眼间都不见了。
每天干完活,许凤和都来找我玩。他讲了许多我从未听过的新鲜事儿。“你们来的时候不好,正是农忙,每天干活忙得要命。”他十分遗憾地对我说,“要是冬天,那才好呢。下场大雪把山封了,山上的野鸡、狍子没食儿吃,都往村里跑。你带着狗,看见野鸡就猛追,它飞不动了,会一头钻进雪堆里,只露着好看的花尾巴……要是有猎枪,就去打狍子,枪声一响,狍子象箭一样跑没影了,这时你别着急,赶快藏起来,傻狍子还会回来,它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……”
“山里有猛兽吗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有哇!狼和老虎都有。”许凤和眉飞色舞地说:“老虎不到村子里来,狼爱进村,它特别奸,象一条狗似的悄悄跟在你身后,趁你不注意,就猛地扑上来,前爪搭在你的肩上,你一回头,它就咬你的喉咙。冬天的晚上,我们小孩出门都拿个脸盆,把盆扣后脖子上,狼就咬不着了。”
我实在想象不出,大雪后的山谷会是什么样子,更想象不出,林海雪原中的动物会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。密林雪野为贫困的山乡孩子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,那是一个对我十分陌生的世界。
半个月的下乡劳动很快就结束了,许凤和恋恋不舍地送我们。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,“你们这儿为什么叫红旗村?这肯定是后起的名字,那它原来叫什么?”许凤和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,他满脸通红,嗫嚅了半天才低声说:“原来叫小人国。”我和身边的同学们都轰然大笑起来。有人问,“你们这儿有小人吗?”许凤和认真地说:“不知道。就是叫小人国。”
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始终没有再去过那儿。据说红旗村早都恢复了原来的名字,叫小人国,我也终于明白,那样童话般的世界,当然要用童话里的名字。不知那儿的小火车是否还在开,小人国的冬天是否还是那般神奇。
《镜泊风》杂志 1997年第3期
江那边的世界
一条江,很宽很宽。
江这边是开阔的砾石滩涂,江那边是陡峭的悬崖石壁,从这边的江堤上朝那边望去,便觉得很远、很苍茫。石壁后面露出朦胧的树影,看上去也蓊蓊郁郁,甚不了然。
那时候,我常从江堤上走,耐不住总要向那边眺望。那石壁后面的树林,会是什么样子?我猜想不出,因此便觉得它很神秘、很诱人,禁不住要在心里编织着各样的图画和故事。
那树林该是一片小白桦吧?林中也该有一块茵茵草地。当晓雾初开,晨曦初露时,那树林、那草地该是童话般的世界;鸟啭鹿鸣,兔跳莺飞,当然也少不了童话里的故事。
那石壁该有几条狭缝吧,顺着石缝该有一条石阶砌成的小径,每当落日余晖,晚风习习,一定会有乡村少女沿着石阶走到江边,用清泠的江水浣衣濯发,坐在树林边低声唱着委婉的山歌。
但是,无论我怎样睁大眼睛,仔细遥望搜寻,终归看不清那石壁、那树林,仍猜不透那江那边的世界。一个风雪弥漫的冬日,我顶风冒雪路过江边,抬眼向江那边望去,只见云雾低垂,天光暗淡,心中不由得又生出一种毛发悚然的阴森感觉,觉得江那边大概是个人迹阒无的幽谷,石壁后面的树林里,应该有一座神河庙,剿匪时抓的那个恶老道,就是在那里。
后来,我终于过了江,到了我无数次猜想、憧憬的江那边,我却意外地发现,在我心目中那么神秘、那么诱人的石壁背后,并没有我所企望的美妙与神奇,石壁没有想象的那么高、那么屹然,树林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、那么飘逸,茵茵草地也没有。漫坡的田野上,是很大一片将要成熟的麦田,黄澄澄的一片。
我觉得很平淡,淡得令人失望,原来那么多、那么美的幻想,一下子都失去了。
这是一个虽然得到、却又失去的世界。得到了真实,却又失去了幻想。
《牡丹江日报》1994年3月31日
镜 泊 石
到过镜泊湖的人,一定都见过镜泊石——一种色黑质重而又多孔的石头,掂在手里,沉甸甸的。
坐着汽车在绿色的林海中,沿着蜿蜒的丘陵公路奔驰,第一眼看见微波粼粼的高山平湖,同时也就看见了这深沉凝重的镜泊石。湖边崔嵬的岩岸,水中嶙峋的暗礁,都是这种石头。镜泊山庄的大门旁,一堵十余米高的石墙,墙上塑着叶剑英元帅的两句诗:“山上平湖水上山,北国风光胜江南”,这石墙,也是用镜泊石凿成的。
在镜泊湖,这种石头几乎无所不在,亭台阁榭用它做基石,山间曲径铺它为路面,就连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渤海国遗址,许多文物都少不了这种石头。著名的佛教石雕艺术品——石灯幢,整个塔身就是用十二块巨大的镜泊石雕凿叠罗而成的。地下出土的舍利函,也是用镜泊石凿成的。
镜泊石是一种火成岩,学名叫玄武岩,也有人叫它熔岩,或者干脆就叫火山岩。据说千万年前,地火运行,冲破地壳,于是火山喷发,炽灼的岩浆从地下溢出,截断了奔流的牡丹江水,形成了镜泊湖这个全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,同时也在湖的周围凝固了蕴量极丰的镜泊石。
镜泊石既是坚固的建筑石料,还是很好的工业原料,它可作耐磨耐酸的铸石原料,也可破碎后经高温烧炼,制成优质的水泥。镜泊湖方圆百里有十余家水泥厂,都是用它作生产原料。
镜泊湖边有一座地下发电厂,那景象煞是壮观。掘开厚厚的土层,凿开坚硬的岩石,延下一千多级石阶,光运出的碎石就堆起了几座小山。发电厂就藏在深深的湖底,在镜泊石的坚硬堡垒之中。沿着石阶走下去,发电机房如同地下宫殿一般,灯火辉煌,机声轰鸣,巨大的发电机组飞速旋转,电能便由此源源输出。当人们坐在明亮的灯光下看电视的时候,谁能想到,这光明与欢乐之中,竟包含着镜泊石的一份功劳。
镜泊石并非默默无闻,其实它早就声名远扬,当年献给宫廷的贡米——响水大米,就是在镜泊石板上的水田中种出的。现在,“响水大米”已被注册成为品牌商标,就连“石板大米”、“镜江石大米”都已成为专门的品牌。市场经济让农民也懂得了乡土特产的优势。
去过几次镜泊湖,我忽发奇想,想找几块玲珑奇巧的石头,放在盘中做盆景,摆在案头当摆饰。谁知找了好久,竟没有一块称心的。那镜泊石,不论大小,都是那么岈岈碴碴,横劈直錾,试着敲凿一下,它又特别坚硬,令人无法雕磨。于是我灰心了,这东西天然拙质,不堪雕琢。
一日去朋友家做客。偶然看到他家的饰物架上摆着几块石头,黑森圆润,形态各异,仔细一看,却是镜泊石。朋友兴致颇高地向我介绍,什么石猴观海、犀牛望月……细心品味,果然似象非条,有几分抽象雕塑的意韵。我觉得很奇怪,本来那么多棱多角的镜泊石,怎会变得这般剔透圆润,憨态可掬。听了我的疑问,朋友嘿然有声,他告诉我说,这几块石头,不是一般的镜泊石,要找它,需在春天水消的时候,去瀑布下流水冲过的地方去找。这石头,不知经过几千年的湖水冲刷,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
按照他的经验,我果然找到了几块神奇隽永的镜泊石。于是,我的案头,也摆上了这大自然创造的艺术品。每当伏案劳乏时,把玩这朦胧奇巧的石头,心里便会觉得轻松许多;偶遇波折,看一看这水渍浪蚀的石头,心中介蒂自然冰释。千年磨一石,这富有哲理的镜泊石,确实能让人得到一点享受,受到一些启迪。
《黑龙江日报》1988年8月16日
本文在1988年黑龙江省“旅游杯”散文大奖赛中获二等奖
镜 泊 月
傍晚的时候,下了一场雨,镜泊湖边更加水气淋漓。说不清这是第几次来镜泊湖了,又是住在抱月湾,景色依旧,林路稔熟,但心境终归是清新适逸的。
听着雨水击打湖面的声响,好象奏着莫名其妙的曲子,劳顿一天的游客不知疲倦,在客房中支起了牌局。同行的小李有些遗憾,“今天是农历十四,如果不下雨,湖边月色一定很美。”我笑一笑,未置可否,但心里想,若有闲情雅兴,雨中的镜泊湖也是别有风味。
不知不觉睡了过去,朦胧中有人在叫:“醒醒,起来!雨停了,陪我出去走走。”我懵懵懂懂,似乎还在梦中,向窗外望去,只见一片银光。果然不错,天晴了,月光朗朗。看看表,呵!快半夜了。我们披上衣服走出门去。
站在湖边的山坡上,让湿润的夜风一吹,浑身立刻清爽起来,刚才的睡意一丝也没有了。抬头仰望夜空,青黛的天幕上,挂着一轮纯净的月亮,似刚洗过的玉盘,又象绣女的花撑,月面隐约的暗影,令人遐想着那仿佛是无比美妙的画面。月亮虽未全圆,但光亮并不亚于满月。身边的花草枝叶上,处处闪着晶莹的珠光,映着月的影子,轻轻一碰,便“扑簌簌”滴下一串水星,象散落的珍珠项链。
银色的月光慷慨地洒在湖面上、山坡上,给宁静的夜色笼上一层薄薄的轻纱。连绵的远山,隐在深沉的夜色里,墨色酣畅,水意淋漓,恰似出自哪位画家的手笔,用巨大的抓斗尽情渲染过一般。白日里一览无余的湖面,现在变得迷迷蒙蒙,神奇莫测,淡薄的青雾如丝如缕,在湖面上轻移曼挪,使偌大的镜泊湖真的变成了一面剔透的镜,又似一块凝碧的玉。静静的湖水荡着细碎的波纹,是调皮的轻风?还是玩耍的游鱼?将月亮的影子摇成一团不规则的光点,让你看不分明,圆月的倩影,就化做这无数斑驳的碎玉,闪烁在静静的湖面上。
我和小李就这样默默地站在湖边,默默地望着这静静的湖光月色。小李是从深圳来,有几分书卷气,平时又很浪漫,此情此景不知是何心境,我也不便贸然发问。静默良许,小李终于一声长叹,似从虚幻回到现实。
他向我问道:“这湖为何叫镜泊湖?”
我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回答。若从史志地名沿革说明这湖名的来历,显然有些太迂腐,有违于这月色的浪漫;若以神话传说中“王母娘娘的平波宝镜”、“靺鞨王寻找红罗女的金镜”来解释镜泊湖的名字,又似乎太飘渺太虚幻,让人疑惑我答非所问。
几经踌躇,我只得转开话题:“镜泊湖的来历说法很多,若有兴趣我可送你几本书,自己找答案。”我指着眼前的抱月湾对他说:“这抱月湾的来历我却可以告诉你。因为这湖湾是象月亮一样圆,周围的湖岸又象双臂一般环抱湖湾,因此便叫作抱月湾。”
小李不再作声。
深夜的湖边,四处静悄悄的。喧嚣一天的镜泊湖,竟有这样静谧的夜,让人难以相信。白日里满湖的游船、如织的游人,都不见了,竟无人消受这清雅的镜泊月夜。
湖边软软的草径,走上去了无声息,我们沿着湖岸的左臂向前走去。周围的一切刚被雨水洗过,变得湿润清新,连心情也被净化了,全无一丝杂念。脚下信步踱去,自由自在,轻松安逸,仿佛天地之间,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“蝉鸣愈静”,真空似的静寂中隐约有一丝淡淡的鸣响,若有若无,仿佛远处瀑布轰鸣传来的余音。忽然想起镜泊红罗女的传说,这微弱的瀑哨该是她柔细的呼吸吧?她大概也深睡了,无意欣赏这家乡的月色了。
前方不远处忽然传来一些响动,定眼看时,树后的曲径上闪出几个人影。走近时,看清是几个搞摄影的,三角架上支着照相机。
小李冲我轻轻一笑,意思在说,“瞧,这也是赏月的。 ”
我终于意识到,流连于镜泊月色的,并非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月,升得很高了,仍然是默默的,带有几分恬澹。近处的湖水和隐在远处的一带青山,构成了一幅恬静的画面。我恋恋地望着这迷人的湖光月色,心中忽然升起一丝奢望:愿那几位有心的摄影师,真的能拍出一些好照片,将这镜泊湖的月夜拍得美一些,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镜泊月,让更多的人喜爱这镜泊月。
镜 泊 秋
国庆时节,秋分刚过,初霜已至。北方的时令来得早,秋的画笔早就调好了浓彩,秋风一起,无形的手便皴皴点点,随意涂抹,转瞬间枫红栎赭,五彩斑斓,镜泊湖的秋天就这样来了。
这是镜泊湖最美的时候。
省城的云奇兄酷爱风光摄影,我们多次向他推崇镜泊湖的秋色,他终于挡不住美景的诱惑,借“十一”长假之机,专程来牡,我们邀上凤程兄,一同去拍镜泊秋。
秋日晨晖中的镜泊湖,碧空如洗,湖水如镜。没有了夏日游人的喧嚣,没有了烈日下的酷热,清静喜人,凉爽宜人。悬崖瀑布还原了高山流水的清雅,山野林木回归了天然无雕饰的本色。盛夏时桀骜奔突的瀑布,忽然变成了温驯柔情的水帘,那意境似鏖战之后的悠远牧笛。瀑口周围悬崖上的灌木,现出红黄橙棕各样秋色,红的如火,黄的如粟,在墨色的石壁上亮得耀眼。不落的松针和耐霜的柳叶还在坚守着绿色,衬着各色秋叶象春花一般蓬勃。
当此美景,谁人按捺得住,大家急切扯出相机,架上“长枪短炮”,分散开来,寻找各自中意的景致。人们常说:“生活中并不缺少美,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。”眼睛其实很容易被诱惑,美不胜收时往往会无所适从,难以取舍。这时候,照相机便显出了优势,在取景窗中,画卷般的立体景物被框选出一帧帧平面的画幅,即使从未学过艺术构图,也能凭直觉抓拍到出色的画面。
云奇兄凭借变焦镜头对着瀑布上下左右、忽远忽近地拍个不停;凤程兄则沿着瀑布深潭的流水向东走,逆着晨光拍水气氤氲的河道、激起雪白浪花的礁石,还有一棵枝繁叶密树形华美且罩在耀眼光晕下的老榆树。
秋水消退,瀑布下游如砥柱一般的一座山石,现在已完全显露出根基。这山石,大小与一栋小楼相仿,瀑布丰盈时,奔涌的激流几乎将其全部淹没,山石的最高处,长着一棵杯口粗的小槭树,在洪水中迎风破浪如一面旗帜,那情景着实令人激动。如今,槭树的叶子已经红了,亭亭地立着,在秋风中飒飒作响,象少女低吟着不知名的恋歌。退到山石背后的江流,浪花腾着乳色的轻雾,将生满青苔的石壁隔在雾气后面,朦朦胧胧,不甚分明,更凸显出山石上小槭树的清纯和靓丽。这独立寒秋的意境,让我耗费了很多的胶片。
瀑布周围大家拍到尽兴,看看日上三竿,连忙转移景点,到瀑布下游一里外的瀑布村。这瀑布村又称作高丽村,是朝鲜族居住的地方。原来村民都住在玄武岩形成的一个峡谷中,近几年搞旅游村民富裕,纷纷在山梁上盖起新房子,传统的村落反倒荒落了。瀑布村江边凭借江水的落差,次第建了三座小发电站,周围景色各有特色,犹以中间一座最为独特。一座黄色小楼是其发电机房,机房以南蜿蜒一条百余米长呈“S”形的石坝,坝内水平如镜,清澈见底。沿着石坝走过去,转过山脚,只觉眼前一亮,如同进入仙境。许是树木种类繁多的缘故,且又是天然混生林,但见树影婀娜,叶色交映,满山秋叶就象一个巨大的调色盘。暖暖的秋阳照着水边青褐色的卧牛石,一潭秋水倒映着斑斓的五花山,五色丛中一丫枝杈擎着嫩黄的细叶,宛若初春的迎春花,又似密云中的一道闪电,无比响亮。这幅景色,简直就是画家笔下的一幅重彩油画。正所谓:此景只能天上有,绝胜佳境不可求。
转过视线,回眸而望,刚才挡在石壁后面的景物也呈现出来,却是建在水边的一组别墅式建筑。几幢小楼构形各异,红墙蓝瓦,绿窗白栏,童话般的境地让人生出无尽的遐想。黑色玄武岩砌成的石墙上攀满野葡萄和爬山虎,朝阳面已是一片火红,背阴处则红绿相间,斑斑驳驳,煞是好看。水潭两岸景色相互辉映,步移景随,别有洞天。
石坝之下则是另一番景象。放眼望去,只见一片巨石的天下,那光景就象昆明的石林。这石林原在水下,现在全都裸露出来,现出一片青白色。众石有高有低,参差错落,走在其间如迷宫一般,且又没有现成的路径,全凭感觉在巨石间攀援,艰险之中带有几分冒险的乐趣。巨石的凹陷处仍然汪着清澈的湖水,巨石的周身蚀刻着水渍的痕迹,偌大的巨石让流水冲刷得棱角全无,不知是几千年的功力,不由人不信世事沧桑。
在这些风格迥异的景物中,我们各选所爱,物我两忘,一时间竟互相迷失。等我拍尽了所有的胶卷,才发现周围已看不到一个人了。太阳早已过午,腹中已是饥肠辘辘,连忙赶回事先约好的汇合地点,云奇兄已回来,凤程老兄却无踪影,等了近一小时,他才姗姗而归,问起缘由,却是误入歧途,绕了很大圈子才找回来。
小发电站门前的高坡上,矗着一座蘑菇形的石柱,恰似坝下石林的标本。先前大家只顾拍摄风光景物,竟忘了摄影留念,现在各自的胶卷都已拍光了,只剩下云奇兄的数码相机还可拍摄,于是在石柱前分别留影纪念。
十月金秋,值此一游,感慨颇多。
游客只知镜泊美,谁人曾识镜泊秋。
镜泊八景,最佳的景观是镜泊瀑;镜泊四季,最美的景色是镜泊秋。
霜林碧水,寒叶秋石,临此佳境,夫复何求。
《中国绿色时报》2003年8月20日
遥望鹰咀峰
暂时没有收录